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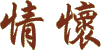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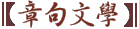


「喬家大院」全劇結構紮實,沒有俊男美女,是至目前為止最細密嚴謹的戲,已經超過雍正王朝與大宅門的水準。
前幾集包頭高樑霸盤的爭奪戰,起死回升的過程已是「危機處理」的經典,連續劇不是電影,一般的戲劇組合原則,
多將最精彩引人的段落放在開始,好吸引住觀眾,若一開始就轉台,很難穩住基本收視率。
「喬」一開始的張力效果遠遠超過其他劇作,叫人直呼過癮!萬萬卻想不到,好戲全鋪攤在後頭。
一、莊周夢蝶
致庸中場退考返家奔喪,一直承受大嫂、大掌櫃眾人央求他執掌家業的重擔,自知不是個從商的材料,但又無法推辭,痛苦掙扎無法定奪。對著水桶裡的倒影,
自言自語:「莊周夢蝶,還是莊周;我喬致庸書生從商,仍是書生喬致庸。」語畢,將整桶水舉起自頭上澆下,如醍醐灌頂般得到啟發,頓然醒悟:以書生的胸懷,
做一個不一樣的生意人。
包頭霸盤之爭得勝之後,能主動登門拜訪邱東家,幫助對手化解危機握手言和。體認化敵為友才是長久和平之道,但只有贏了全局,足以制敵死命之際,才能提出談判的條件。
當刀柄在我,刃敵要害,向對手說「yes」比說「no」更難得、更偉大!寬容化解敵對,攜手和平共榮,正是仁者的胸懷,智者的遠見。商場如戰場,徹底殲敵絕不是趕盡殺絕,
只是屈服其戰鬥意志,使資源為己所用;消滅對手最經濟有效的手段,只有「化敵為友」,事後也證實,邱東家對他感佩一輩子。
包頭的舖子、產業穩住了,接連在制度上大刀闊斧,違反傳統的逆向操作,拔擢新秀,讓跑街的馬荀主掌包頭對外一切事業;建立夥計身股分紅制度,讓員工主動恪遵規範,
效命東家推展業務;之後為了完成匯通天下的宏願,充分授權潘為嚴,不過問一切經營、不聽信任何閒言,這不是容易的事。知人、善任是領導者最重要的決勝條件,
在這方面他兼具漢高之智、唐宗之量,才是他去凶化險,成就事業的關鍵。
致庸對馬荀道:「馬大掌櫃,你知道我們商人怎麼濟世救民嗎?我們要有大志向,大抱負,要做天下那麼大的生意,為天下萬民生利,這就是我們商人濟世救民之道!」
馬荀點點頭道:「東家,現在馬荀才真正明白,這一生該如何做商人,東家你就瞧好吧。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難,馬荀都要把喬家的生意做進蒙古大草原,
幫助東家做成天下那麼大的生意,為萬民謀利!」喬致庸比美國福特公司(1903年成立)提早四十多年,悟得員工與公司攸關一體的道理,以直接入股分紅,
改善員工福利,化解勞資矛盾,提升競爭能力。
孫、潘兩人之格局、視野、人格特質完全迥異。孫的特性偏重在:危機處理,近程的傳統經營。潘的特質著眼於:洞見未現之機,察勢未趨之前。兩人都是幹才,
但潘志向高邁,品行磊落;孫抱殘守缺,見利壞德。但致庸都能讓其發揮所長,於不同的時期決定至當的人選為己所用。孫使喬家起死回生;潘造就喬氏票號的霸業根基。
人性無完美,缺失弱點在所難免,領導者主導大局成敗,就應懂得如何將事業成功建立在共同之優點上、利益上。而不能只見部屬之缺失弱點,大嘆無人可用!
最高境界之領導就是如何讓每個人的優點潛力發揮出來,全力以赴、齊心投入,為共同之目標各司其職,恪竟其功。領袖人物,不應該要求別人依照怎樣的哲理,
甚至自己主觀的定見去處理人性。宜掌握人性本質,將其運用到自己所欲領導的方向上。孫茂才私德固然不好,也許是奉養老母生活壓力所致,但不影響處理大格局的智慧。
一代名相管仲,也有這方面的瑕疵,但是知己好友諒解他;賢明君王信任他。
世上最偉大的功業都是如此成就的:李世民之前沒歷練過皇帝;喬致庸打牙根就沒想要致富經商,只因為事事用心、善於任人、有天分、有良知、有理想,他們都是最好樣的。
二、巴山夜雨
李商隱的夜雨寄北:「君問歸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,卻說巴山夜雨時。」原是藉雨夜孤寂的情愫,抒發異地懷思的情景。致庸性情中人,
平日言語率性舉止很少正經,卻有兩次表情嚴肅地寄情這首詩句,絕大多數觀眾煙霧朦曉,只當成劇情外的旁生。對象都是孫茂才,致庸卻又沒有明講。
孫茂才的人品,在第一集賣花生時就已經詮釋定位:使假秤偷斤兩的小人。騎著小毛驢深夜前來投靠,致庸及下人都沒當回事兒,待出謀劃策成功後,
獲得致庸及團隊上下一致信賴,自以為遇得孔明,親自替他提鞋,自己卻光著腳出門。武夷山販茶以後,孫茂才就是主宰決策的「軍師」,喬家也給予最高的年酬謝銀,
賓主融洽如同手足。
自蒙古草原、恰克圖賣完了茶葉賺得暴利,致庸無意間認知銀票的好處,決意開發票號,實現匯通天下、貨通天下的宏願。茂才分析風險堅決反對,
請求去臨江茶山全權督辦茶務。致庸去北京開創票號,面臨老號廣盛源的重重阻撓,連日以金元寶、銀冬瓜強來兌銀,眼見銀庫存兩不足,徹夜未眠不知如何是好。
翌日緊要關頭時,幸得岳父出面解圍。但事後心有餘悸,夜雨階前獨聽點滴,難以入眠不由得寄情「巴山夜雨」的詩句,期盼好友「何當共剪西窗燭」的情誼與依賴。
天亮送走了岳父、玉涵,隨即打發鐵信石回程去臨江接回孫茂才。
第二次是在大奶奶被孫茂才說動,提出收回喬家事業,由茂才獨攬經營、對半分紅的構想,致庸識破其陰謀,狠下心要將他攆走。那一夜大雨傾盆,致庸壓抑下已經爆發的衝動,
握住玉涵的手,寫完「何當共剪西窗燭,卻說巴山夜雨時。」的詩句,對一起創業、甘苦共嘗的鐵哥們,發出內心的感傷。
天一亮,將百般羞辱後的茂才轟出門去,攜手多年的孫軍師,連滾帶爬地被踹下台階,牽著小毛驢走了。致庸怒罵:「你知道她是誰?雖是我嫂子,
但她自小把我帶大,就是我娘。」致庸說的是沒錯,但昨夜裡曹氏冒著大雨來給孫先生送棉襖,茂才喜極一再致謝,曹氏:「孫先生太客氣了,上回你打廣州給我捎來的衣料、
首飾,還沒謝你呢!」這一段戲裡沒出現過,導演藉此機會一語帶過。孫先生入冬腿常發冷,之前曾親手給茂才縫製過錦緞護膝,顯示礙於吃人的禮教與家規,
兩人的心願是不允許也沒指望的,但大奶奶認定孫先生:於公是家業興旺的得力助手,於情何嘗不是內心私許託付心事的摯友知己。
當家做主的遇到這等事,當然要決斷處理,但也不能完全不念舊情。數十年來,多次為喬家出謀紓困、全國奔波、獨當一面、營救出獄…,正如孫茂才之後所言:
「當初東家只要稍稍的寬慰我;稍稍對我客氣點,我興許會念點舊情。他對我孫茂才做的真是恩斷義絕!」他話雖如此說,還是巧妙機智的保全致庸出獄,
他對致庸還是有情誼的,絕不同於崔鳴十那般雜碎心腸,也再次展現危機處理的能力,這可不是潘、曹、馬、高諸掌櫃智慧、能力所及的。
新婚之夜,當著曹氏殉節的遺體,哀嚎真愛無罪的控訴:「我對喬家沒有割捨不下的,最惦念的就是你,你是我在這世上唯一珍重的!」搶天呼地萬念俱灰,
接著嘔心瀝血的哭訴冤屈:「在你們喬家眼裡,我不就是個賣花生的嗎!但當年貢院一見如故,數十年南北奔波、出生入死,為喬家壘積半壁江山,我沒功勞,
也有苦勞啊!」其實他不但有功,而且也有恩於喬家,而他最後所爭取的也不過就是每一位男人基本的尊嚴:「去除自卑,地位平等。」
致庸的決斷正確,但過程、手段全錯了。君子絕交不出惡言,何況小人是得罪不起的,致庸再次打入死牢,罪有應得。
在包頭霸盤之爭,為了騙邱東家上鉤全力買回高樑,好讓喬家早日解套,但邱東家老謀深算始終按兵不動,致庸情緒崩潰都急哭了,想結束一切罷手回家團聚。
待後續五十萬兩銀子運到,一日孫茂才:「東家,皇上準備攻打準葛爾部,我們光給大軍準備糧食是不夠的,還要大量準備馬草。」致庸恍然大悟,笑道:「這招太損了!
我現在知道誰最壞了,太壞了你。」孫:「東家,現在還只是個傳言,咱們還得想轍,把這事兒給他做真了、做大了。」致庸:「你實在是太壞了,又壞又聰明。」
孫得意感慨之餘:「我自個兒想起我自個兒來,我都覺得我可怕。」
將邱家徹底撂倒之後,馬荀的敏銳能從一穗長滿蟲害的高樑,見到明年的市場商機,是商業技術層面的先覺;茂才的遠慮預測出得勝後即將接踵而來的危機,
主張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立即言和放過對手,是謀略層次的智慧。這一段劇情:表面是霸盤戰的運籌演謀,骨子裡已將孫、喬二人的才幹思慮、人格特質比出高低、
分屬歸類,你致庸怎能不在意、不防備孫的本性與底細。
最後一集裡,白髮蒼髯的致庸樹下沈思,一臉悲戚遠望著荒郊山野,追憶如煙往事,嘟囔出數十年來壓在心底的悔意:「茂才啊!茂才!聽說客死他鄉,連個送香火的人都沒有,
也沒留下後,怪可憐的…。」也算交代了茂才悲情的一生。
三、頓悟禪悅
論演藝技巧,雷格生所飾演的陸大可當屬翹楚。他不像焦晃、李保田都是定型的「好」演員,不論演任何角兒,都甩不掉康熙、羅鍋附身還魂的影子,連手勢、語氣、眼神都改不了。
雷格生就不然,「大宅門」裡陽奉陰違的貪瀆無厭;「大清藥王」裡專業盡職的厚道老成,恰到火候又十足入味。在這戲裡飾演第一摳門兒的守財奴,守著巨大財富省食節用,
落入鴿糞的一粒飼料也要拾回來;泡茶之前都要抓回幾粒茶葉,連茶碗也是個破損帶缺口的。
投資的錢都十拿十穩的使在刀口上。致庸第二次去包頭,轉眼帶去的銀子又都被邱東家換成高樑,派人回去請玉涵再籌借三十萬兩。玉涵接到告急立馬回娘家求救,陸大可先是不肯,
玉涵哭鬧耍賴威脅:「以前借出去的五十萬兩,你也別想拿回來,就當是打了水漂了吧。」,陸大可危言正色:「你再鬧北京的事(放假消息)我就不管了」,後又裝腿疼,
玉涵給老爹搥著腿,陸從床上坐起:「我仔細算了算,還是不能借你三十萬兩啊!」玉涵頓時垮下臉洩氣了。接著又說:「我要借給你們五十萬兩。」玉涵目瞪口呆地聽,
「我算給你聽聽,他們邱家能有多少銀子?就算把外地買賣的餘銀都拉回包頭再加上包頭的,撐死也就是七、八十萬兩;我要是借你三十萬兩,加在一塊那就八十萬兩,
最多跟他打個平手。我要是借你五十萬兩,加起來…」玉涵搶著說:「一百萬兩!」他點著頭說:「準能打敗他!」玉涵欣喜忘形,破涕為笑,抱著老爹撒嬌。
「高興了是吧!孩子,爹為啥這麼做,純粹是為了保住我那已經借出的五十萬兩花花的銀子。」人又躺回去:「怎麼不搥了,繼續搥,這兒!這兒!舒服啊,這生意做成了無底洞…。」
演的高潮迭起,生動自然,真是氣象萬千。
「知彼己,多勝算」邱家陸續自太原府、包頭、庫倫等處運來銀子的總數,果然只有三十萬兩,陸大可算計的精準無比,唯有五夷山販茶沒跟著入股,事後懊悔莫及。
之後多次為女婿解圍紓困,最經典的一次,是對付北京票號廣盛源的那一招,探知其銀兩已大筆放貸之後,及時亮出銀票,只做出匯兌姿態,讓廣盛源臣服低頭,
兵不刃血化解危機,不傷和氣不結冤家,真是商場戰略高手。危機處理的最高指導原則:不是重創後完美的善後,而是化解危機,不讓問題發生。
精打細算省了一輩子,在女婿身陷死牢的關頭,將四百餘萬兩的全部家業,緊急抵押兩百萬,搭救致庸。臨終前已穿上大拍賣時花一兩銀子買的壽衣、
拍著才花二兩銀子買的那口薄棺材:值啊!告知女兒:「看到致庸匯通天下的大格局、大志向,自覺慚愧,此生算是白活了!」依然牽掛不捨地:
「我走了!不能再護住他。你要替我護住,幫著他實踐宏願、成就一生的大事,也是咱父女倆的大事。」望著女兒的背影,想起那一夜為了開票號,
她來借銀子時說的話:「為了這個了不起的丈夫,跟著他吃苦受罪,也是我的福氣。」內心愉悅無比的逝去。是「朝聞道,夕死可也!」的欣喜過望,帶著成佛悟道的滿足,
離開了人世。
榮華盡頭是悲哀,弘一大師圓寂前的「悲欣交集」,是勘破無常與回首有情的錯綜交織;陸大可俗不可耐度了一生,但因豁然開朗,走的卻「心無罣礙」,他以一生的心血、
積蓄,替寶貝閨女,「摳」來這不世出的好女婿,是個英才,值啊!
四、不均必寡
財富本身不是罪惡,但擁有過多的財富,即使來源正當合法,就經濟學生產與分配的立場,是製造貧富差距的亂源。何況古今中外的鉅商豪門,幾乎都是官商勾結的產物,
只有靠制度配合、利益互惠才能在短時間兼併壟斷鋪天蓋地的財富。喬家也不例外,庚子年慈禧西幸接駕有功,將全國匯銀業務、山西地方稅銀,全權指定喬家經營,
之後又接管部分關稅。財富越集中,差距就越大,赤貧就越多,延伸的社會問題就越殘酷、越複雜。廣大群眾為了存活或過的安定,任由富豪廉價奴役、凌虐、驅使,
這時候財富就是罪惡的化身,腐敗的政府、貪瀆的官員全是幫凶。
通貨需要不停的進出、到處的流動,流動越是頻繁、業務越是廣袤就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,嘉惠更多的生靈。否則囤積過量的財富,只是帳目上數字的變化,對自我、
對社會沒有實質的獲利意義。致庸晚年的銀庫富可敵國,由玉涵攙扶著巡視看不到邊的金銀,只一路罵道:「呸!這些禍害人、不要臉、無用的東西。」並沒有覺悟到如何放下,
如何有效利民利己的計畫運用出去。使家家有餘糧,庫庫有存銀,藏富於民,國勢自然強盛,用不著抱怨:「票號的營利,都是幫朝廷將銀子匯給洋人賺來的,長此以往,
銀子全賠給了洋人,咱還能上哪去匯銀子。」
去包頭的路上,致庸從店家伙房收留的高瑞,他爹娘餓死在路邊,他那年還小,是一碗熱湯救活的。這不是戲言,歷史上這種事很平常,沒被活生生的切割賣了吃掉,
就算幸運的。俺小時候都經歷過,自己的親弟弟就是逃難餓死的!百姓家平常只能餬口,遇上戰亂、荒年,救濟不上只有一死。財主只會守著銀兩或廣置家產、兼併土地,
缺乏「通貨」的觀念,更妄想慈善事業輔導。遇上災民知道捨粥已是菩薩心腸的好地主,不懂得如何下放財富:普及基層教育、創造就業機會、提升社會福利及平均所得、
改善產業型態及生活水準,以均富共榮消除災民的肇因。放下財富就是放下罪惡,比放下屠刀更能立地成佛。
This country will not be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ny of us to live in, if it is not a really good plac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.(若不能讓大家過上好日子,
就別妄想自家安穩。)羅斯福總統的均富思想,是一句警語:「指出民生的方針,圈定革命的對象,預言動亂的源頭。」當地主過足了大煙癮,前呼後擁、美酒佳餚,
從大院戲樓高臺看出去的「view」,全是陋巷、破屋、餓殍及成群等待捨粥的難民,這深宅大院能住的安心嗎?明白告訴你:「外有高牆、內有護院,安心極了!」
這就是他集中財富後的安全感與優越感,否則也會淪落街頭乞討。1949年前後中共的土改政策,看準了階級對立,正本清源直取要害的猛藥,確實是慘無人道,
但是幾千年來易子而食、億萬冤魂的人道又在哪?
李自成造反後的掠殺;馬克斯的思想理論基礎;共產主義的極端教條,當然都不對。但又為何都能成功?都能號召廣大群眾效死追隨,煽動起世紀風潮?
他們都是被走投無路的仇恨逼出來的。你不是「他們」,你無從想像那種仇恨有多痛!
五、返璞歸真
致庸生性善良,有理想抱負又講義氣。一生為人正派、耿直、真情、至性,可自對待官府及處理孫茂才、劉黑七、江雪瑛等事件上顯現出來。廣州分號開幕當日,
得知孫茂才應允讓官府哈大人入了銀股,氣急敗壞地說:「這是行賄。從今天開始,我喬致庸不再乾淨了!我就成了我最不想成為的那種人。」礙於現實與大局,
他只好默認接受既成的事實。為了賑濟災民,不惜傾家當產,他知道:當全天下的人都成了災民,自己也會淪為災民的道理。就衝這些人格特質,他就不「配」當個商人。
商人重利輕別離,其實商人輕視的不只是親情而已,除了商機、利潤,悍然不屑一顧。致庸千里販茶是新婚直後,大嫂為了借貸陸家的銀子,硬生生拆散美好姻緣,
喬家尚且如此!這是為商求存牟利的本性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致庸堂姊夫水長青:財大氣粗,唯利是圖,吃人不吐骨頭。整日票戲嫖妓尋花宿柳,獨子元楚天賦書卷喜好上進,
卻不准其上學讀書,說讀書不是正道,正道就是學生意賺錢致富,聲稱若再發覺兒子讀書,就打斷他的狗腿!也正是「從商致富易,暴富貴氣難」的道理。
「貴」在富人心眼的定義:「我有的,你們沒有。」,有錢能使鬼推磨,財富是無所不能的,具體表現在「賣富」的奢華與享樂上。但最終都還會明白:
再多的錢也換不來最想要的青春生命。致庸指著滿庫的金銀大罵,內心的吶喊,何嘗不想喚回舊日的情懷。
終歸是秀才出身,讀書人比起一般俗物有較深層的領悟,錢財不但喚不回歲月,更買不到智慧、學識與品味。雪瑛比致庸更早覺悟六十多年,當她繼承了何家產業,
堆滿地窖的庫銀使她悲哀的癱地不起,心碎了!哭訴:「現在才有這麼多銀子,有什麼用?」在她心中世上的一切,沒有一樣能比得上致庸的愛。
一個風燭殘年的寂寞老人,夢見自己化成一陣風吹進大院,一切全變了,誰也不認識。醒來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,對著鏡子訴說自我一生的定位:眼前的莊院、
財富不是他人生追求的志趣,到老都覺得一生白白浪費了自己的勇氣、智慧、才學、熱情,沒能將自我成就為平淡樂道的李白、王維、杜甫…安心過上自己的日子,
身後配饗千古永懷的「尊貴」。挑在結尾再次闡釋故事開始「莊周夢蝶」的劇情,述說:「往事如過往清風,從商了一輩子還是念茲在茲---高邁不羈的書生願望。」,
首尾呼應,手法率然。
每逢出遠門,致庸都揚著脖子高喊『走咧!』下達車隊出發的號令。當朝廷解除了圈禁令,去西北押送糧草的那一次,也是最後一次遠行,那聲「走咧!」喊的又長又悽慘,
這數十年把熱血好動的工作狂,可憋死了。人老了,面對死亡早已心如止水,死亡只不過是不再回來的走咧,路途比包頭、五夷山、西北、恰克圖都遠,但時間很快,
還來不及感覺就「到咧!」。玉涵去野外送飯,倒地死在半道上,致庸只是淡淡地語帶責備的說:「不就是送個飯嘛,急啥的!這不…。」原作致庸結婚六次,
都是續弦,按「正史」玉涵早已過世,編劇如此結局挺好的。喬家上下忙著玉涵的喪事,致庸在廊下躺椅假寐,表妹雪瑛前來弔喪。此生唯一的青梅竹馬、
觀音廟裡的山盟海誓,往事不堪回首,只能互話家常。年輕時熱戀的激情早已乾涸,沒有起伏的情慾,平靜中感應出當年互許終身的真摯與曾經驚天動地的熱愛,雪瑛是他永遠的牽掛。
問世間情是何物:那一日,致庸覺悟到不得不娶陸家小姐,心如刀割的痛苦,在地上打滾、傻笑、哀號;那一夜,大嫂接雪瑛來讓兩人見上最後一面,她披上嫁衣裳,
緊緊抱在一起:「即使喬家一貧如洗流落街頭,也要嫁過來,一樣過的歡天喜地…」,致庸無顏以對,開不了退婚的口:「不管發生甚麼事,我的心永遠都是你的…」;
新婚夜,拋下沒揭蓋頭的新娘,去她樓下喊出他心裡唯一的愛:「雪瑛!」。
這一日,他為愧對誓言而跪拜不起:「這一生我上對得起國,下對得起家,唯一愧對於你。」她心滿意足了,回以淡淡滿足地笑容離去。『年輕的時候,
若不曾有過刻骨銘心的愛戀,到了老年,寒冬的夜晚會很冷!』雪瑛晚年孤單一人,但剩下的冬天會過的很暖和。致庸正要送行,卻翻身倒地,臨別依依,
望著捨不下的牽掛。這回是真的走咧,就像午後的夢境,化作一陣風飄然而去。走的快,到的也快,只是走的百感交集,「牽掛」還來不及感覺完就到咧!
繁華瞬間如夢一場,世上又有幾翻空忙。
挑剔喬劇的缺失:
一、喬家大院是喬致庸發跡以後整建宅院的大手筆,是山西旅遊團的景點,館內共有院落19進,房屋300多間,全宅遊覽約需四小時以上。戲亦以此為名,
只在最後說了一句:「賺了些銀子,修了這大院…。」更不應該的是,全程始終都在同一場景(『大紅燈籠高高掛』的宅院佈景)拍攝,略草率了些。
「在中堂」的匾是庚子年以後的事,卻一開始就在「舊宅」出現,屬考據的疏忽。
二、武夷山屬閩江水系,由西北向東南流經福州出海;湘江是長江水系,由南向北流經洞庭湖入江,中間隔著江西省。劇中販得茶葉,
召集百餘民船由武夷山經湘江北返是一條不通的水路。
正確的路線:先由武夷山陸路至南昌---換贛江經鄱陽湖水運入長江---過漢口溯漢水而上---至襄陽。
三、大奶奶曹氏,嫁到喬家時致庸才七、八歲。合理推算:致庸比曹氏小十歲左右;比景泰大十歲以內。但戲裡展現的,未能考慮這實際的數據因素;
元楚聰慧好學,後續未見交代,卻讓資質平庸的景泰中上狀元,都是編劇的疏忽。
四、依清制一至五品得對官員之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及妻室授以誥命,存者為誥封,歿者稱誥贈,是為官光宗耀祖、封妻廕子的榮典。
紅樓夢第十三回「秦可卿死封龍禁尉,王熙鳳協理寧國府」,寫的就是這事兒。秦氏是賈蓉之妻、賈珍之媳,…「賈珍因想著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,
靈幡經榜上寫時不好看,便是執事也不多,因此心下甚不自在。」…,問題就見這「執事」二字上,那年代是有王法的,尊卑分寸不容僭越,不是只要有銀子、
是首富就能恣意妄為,執事就是儀仗:「帝王、官員外出護衛的人數及所持的旗幟、傘蓋、武器…等等。」,雖無實際用處,卻又缺少不得,用來擺譜兒撐場面的。
賈珍為了讓殯喪風光,花一千二百兩銀子捐了個五品官。…「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,領憑回來。靈前供用執事等物,俱按五品職例。
靈牌、疏上皆寫『天朝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』。」
喬家大奶奶自己有兒子,去世前景泰已中狀元若是六品,母親可封「安人」,就以七品官,曹氏也該封授「孺人」,其父致廣也能敕贈「承德郎」,致庸上墳時,
墓碑上卻刻著:「先嫂曹氏月枝之墓」。正確而傳統的是夫妻歸葬,由孝子具名,碑文:「顯考、妣諱…加上誥封」,世上哪有小叔替嫂子具名立碑的道理。
禮記:「生曰父、曰母、曰妻,死曰考、曰妣、曰嬪。」鏢局老英雄戴二閭,守墓事孝,墓碑上卻是「先母…之墓」,應該是「先妣」;陸大可的墓碑也是「先父…之墓」。
「雍正王朝」裡也見相同失誤,編劇的知識、倫理水準疏忽的太離譜,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後遺,這不是件小事。
2006年7月4日

